
站在云端当下 书法/漫画 李法明
彼时,2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让习惯躲在角落里的工人诗人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姿态站在了诗歌朗诵的舞台上。19名工人在北京向世界朗读的消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热烈、期待。
此时,3月21日、22日,本打算让他们站在天津大剧院舞台上朗读自己的诗歌,却因为售票不过10张,而被迫推迟至5月23日、24日。
工人诗歌,再一次经受了社会的考验。工人诗人们,再一次无奈地面对了现实。
巷道爆破工、酿酒工、炼钢工、锅炉工,
他们把劳动刻录在诗歌里,却因少人倾听而不得不停下歌喉
老井,安徽淮南矿业集团潘北项目部井下供电队的一名电钳检修工人,今年46岁。2006年他的一组《煤雕》诗歌获得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的提名奖,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诗歌同他本人一样,静静地躲在煤矿的巷道之中,不见光。笔者给他打电话时,并没有从电话那头听出太惊讶的声音。他说从北京回来,就不断有当地媒体采访他,但这却让单位领导不满,“他们说我接受采访应该经过单位同意,我觉得休息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在家的时候,人家打电话过来说要采访,我还要跑到单位征求同意,那太麻烦了。”老井说他是合同制工人,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体制内的”,但这份体制内的工作并没有带给他优越感,而诗歌作为一种爱好,是打发寂寞、落魄时间的最好方式,也充实了他的内心世界。他说:“我想写出好的作品,至于会怎样,我不强求,我也不拒绝。”
相比起经历过半辈子风霜考验的老井的冷静,1985年出生的吉克阿优倒是更乐观地对待这场带给他自豪与信心的活动。这位刚三十而立的彝族小伙子说话轻快,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更显得轻松、自在。2012年四川省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他的诗歌《漂泊的灵魂》获得二等奖,他笑着说:“从北京回来,工友、领导还有一些地方官员见面之后都夸我,说我是难得的人才呦。”说到未来,他说:“以前觉得梦想很渺茫,现在好像找对了路,虽然不知道以后会带来什么,但写打工诗歌这个路子是对的。”
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炼钢厂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农闲时当锅炉工的白庆国、14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以及不久前坠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们都是普通工人,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把工作刻录在自己的诗歌里;他们的诗歌诉说着他们的尊严与苦闷。
然而,皮村的那次活动并没能带给他们持续的好运,当他们准备自信地站在更高的舞台上时,却因无人问津而不得已推迟了。没人买票的现实,再一次说明,大众漠视的态度,也再一次毫无意外地挑战了工人诗歌的尊严。
比起一些专业诗人,他们的诗歌少了功力却多了真实,
“在文学领域,他们是一群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
如果说皮村的那场工人诗歌朗诵会,是工人诗人们自发的一场活动的话,那么,把这群“泥腿子”们的诗歌搬进天津大剧院这样的一座现代化的高端剧院舞台,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可临开场还剩两天了,票才只卖出去了10张,600多张的空位,又让人心寒了。
天津大剧院企宣杨思思说,“虽然票价从180元,降到120元,又降到80元、60元、50元,但还是不得已要推迟演出。在文学领域,他们是一群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
对于诗歌朗诵会被推迟的事情,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更为冷静。他曾建议朗诵会就叫“屌丝诗会”,他说:“他们是一群草根阶层,比起一些所谓的专业诗人,他们的诗歌不造作、少了功力,多了真实,他们的诗歌才更有价值。”但诗歌的价值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商业利益。钱程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剧院必须关注诗歌,但诗歌遇冷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工人诗歌遇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上世界80年代,曾是“工业田园”与“共和国之子”的时代,那时的工人诗歌出自舒婷、梁小斌、于坚等人的笔下。那时的流水线上跳动的是音符,烟囱里的浓烟代表了一个城市崛起的痕迹。舒婷在《流水线》(1980年)中描述:“在时间的流水线里/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我们从工人的流水线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在我们头顶/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在我们身旁/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那时工人有作为城市主人的自豪感。
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工人遭遇下岗,可工人诗歌仍然艰难地保持着自身的体面。老井的诗歌《地心的蛙鸣》里写道:“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仔细听,却没有任何动静/我捡起一块矸石扔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蛙鸣”、“柳塘”和“月光”这些意境很美的田园风光,使冷冰冰的煤层拥有了生命的气息。
可是自本世纪以来,工人诗歌逐渐淡出了高贵的舞台,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大规模流向城市,诗歌成为他们抒发内心苦闷与彷徨的阶梯,读者从这些诗歌中读到的更多是工业之痛和个体的绝望感。在郑小琼的《流水线》中,工人在流水线上变成了“流动的人”,他们像犯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工位号码。“流水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她们,或者他们,相互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丝,塑胶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染上职业病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
“这些诗歌,就像它们的作者一样,长期消隐于光亮之外”,
但对劳动者的创作,人们需要“怀着谦卑的心态聆听”
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一份体面的工人诗歌不知从何时开始变成软绵无力的挣扎了。虽然喧嚷的社会不断地被乌青体、梨花体,余秀华、许立志等诗歌和写诗的人“打扰”着,但这个碎片化的社会,并没有给诗歌注入多少活力;虽然几亿的农民工不断地涌入城市,工地上、马路上、走街串巷中,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但面对城市的冷漠,不知是他们早已习惯还是无可奈何?
为什么工人选择用诗歌来自我表达?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繁重的劳动之外,这是最低成本、最直接的诉说方式。
诗歌评论家、诗歌朗诵会的主创人员秦晓宇说:“过往30多年,中国工人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长期被边缘化,被歧视和漠视。这3.1亿人,就工作生活在我们周围,却仿佛十分遥远。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代中国工人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一些佳作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严重忽视和低估,在当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工人诗歌难觅踪影。这些诗歌,就像它们的作者一样,长期消隐于光亮之外。”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还有人在帮助他们,给予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还有人肯关注他们。一位金融行业的刘先生买了票,他说:“打工者虽然不是主流的声音,然而在中国确是庞大的,是冰山下沉默的群体,他们需要被关注,需要被倾听。他们的生活境遇不是很好,但仍能发出对生活的爱,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我们的生活需要信仰和支撑,我是怀着谦卑的心态等待聆听这场演出的。”
当笔者把这些话转述给工人诗人的时候,他们或沉默几秒钟或腼腆地笑,朗诵会被推迟,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他们说:“是推迟,又不是不办了,准备时间久一点才更充分,我们本来就是默默无闻的诗歌爱好者,能有机会总是好的。”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群可爱的工人诗人们并没有因为坎坷和磨难而心灰意冷,他们还是常年站在工业生产线上,默默地用诗歌倾诉着自己的心声,他们希望被关注,却又不强求。
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浮躁、喧嚣的社会,我们能否静下心来聆听他们的苦痛,能否放慢脚步体味这份人生的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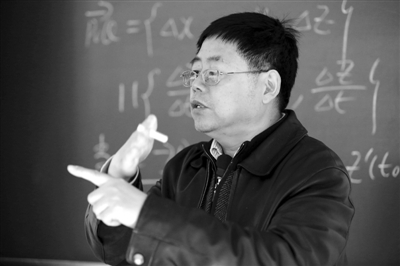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